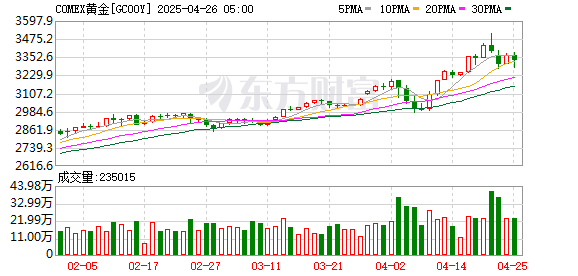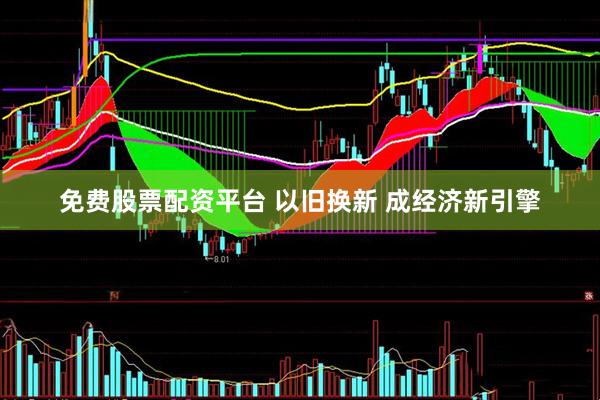1.
那是冬至,也是我这二十四年来,过得最冷的一个晚上。
窗外的北风像哨子一样尖厉,拼命往筒子楼老旧的窗缝里钻。屋里的灯光昏黄摇曳,桌上那盆热气腾腾的饺子,成了这个家里此时唯一的暖色调。
“啪!”
一声清脆的耳光声,生生把这仅有的一点温情给震碎了。
我猛地抬头,看见妈妈捂着左脸,不可置信地看着奶奶。那一巴掌极重,妈妈的嘴角瞬间渗出了血丝。
原本端在妈妈手里的醋碟被打翻,黑褐色的醋汁溅在她洗得发白的毛衣上,像一朵朵干枯的花。
“吃吃吃!就知道吃!”奶奶站在餐桌旁,干瘦的手指指着妈妈的鼻子。
展开剩余90%那只手还在剧烈地颤抖:“连个香油都舍不得放!你是不是盼着我早死?这一天天的苦瓜脸给谁看?滚!带着你的穷酸气滚出我的房子!”
空气在那一瞬间凝固成了冰。
我那个一向以“孝顺”著称的爸爸,正夹着一个饺子停在半空。
他慢慢地把饺子放回碗里,没有看妈妈,也没有看奶奶,而是盯着桌上的那摊醋渍,整整沉默了三秒。
我气得浑身发抖,刚想站起来替妈妈那一巴掌讨个公道,爸爸动了。
他站起身,没有像往常那样和稀泥,也没有低头抽那6块钱一包的闷烟。
他动作缓慢而坚定地脱下身上那件深蓝色的工装呢子大衣。
那件大衣是他十年前买的,领口磨破了边,袖口沾着洗不掉的机油味,那是他作为老钳工特有的味道,也是这个家最安全的味道。
爸爸走到瑟瑟发抖的妈妈身边,把带着体温的大衣轻轻披在她身上,宽大的下摆遮住了妈妈衣服上的脏污,也裹住了她摇摇欲坠的尊严。
“媳妇,穿上,别着凉。”爸爸的声音沙哑,却异常清晰。
然后他转过头,看着那个刚刚还不可一世、此刻却喘着粗气的奶奶。
“妈,如你所愿。”爸爸的眼神里没有愤怒,只有一种我看不太懂的、深不见底的悲凉,“咱们今天就搬出去。”
2.
这一刻,我等了太久,却没想到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。
收拾东西的时候,我几乎是带着报复性的快感。我把所有的衣服胡乱塞进编织袋,故意弄出很大的声响。
奶奶就坐在客厅那把旧藤椅上,背对着我们,一言不发。
那台老旧的收音机里正放着评书,咿咿呀呀的声音在死寂的房子里显得格外诡异。
我经过客厅时,恨恨地瞪了那个瘦小的背影一眼。
我想起这半年来她的种种“恶行”:嫌弃妈妈洗碗费水,半夜故意把电视开到最大声,甚至上周趁我不在,把我的考研复习资料当废纸卖了五块钱。
邻居都说赵老太太变了,变得尖酸刻薄,像个老巫婆。以前我不信,现在我信了。
“晓晓,别拿那个暖水壶了,那是你奶用惯的。”妈妈红着眼睛小声提醒我。
“不拿就不拿!留给她,让她守着这破房子过一辈子吧!”我赌气地把壶重重放下。
爸爸提着两个最大的编织袋走在最前面,妈妈跟在后面,还穿着爸爸那件深蓝大衣,显得空荡荡的。
走到门口时,爸爸的脚步顿了一下。
他没有回头,只是背对着奶奶说了句:“妈,药在电视柜第二个抽屉里,红花油在茶几底下。变天了,腿疼别硬扛。”
藤椅上的背影似乎僵了一下。
但她依旧没有回应,只是收音机的声音似乎被调得更大了,像是在掩盖什么。
我们就这样走进了冬夜的寒风里。
3.
那个晚上,风大得能把人脸皮割破。
我们在离家三公里的地方找了一家廉价的小旅馆。房间很小,只有一张床,墙皮脱落了一半,散发着一股霉味。
一进屋,妈妈终于忍不住了,坐在床沿上捂着脸痛哭起来。
“建国,妈她以前不是这样的……是不是我哪里做得真的太过分了?”妈妈还是那样,永远在自己身上找原因。
我气不打一处来:“妈!你被打傻了吗?她就是老糊涂了!就是恶毒!你看看大伯,半年都不露面,她还天天念叨要把房子留给老大。既然她那么喜欢大儿子,就让大儿子去伺候她啊!”
提到大伯,房间里的气氛更压抑了。
大伯是家里的长子,从小就被奶奶捧在手心里。半年前他说去做生意,借遍了亲戚的钱,然后就人间蒸发了。
也就是从那时候起,奶奶的脾气开始变得古怪。
“行了,别说了。”爸爸坐在唯一的椅子上,低头点了一根烟。
烟雾缭绕中,我看不清他的表情,只觉得他苍老得厉害。
“爸,你早就该硬气一回了。”我走过去,蹲在爸爸面前,“今天那一巴掌,打断了咱们家最后一点情分。搬出来也好,以后咱们一家三口过,不受那个气。”
爸爸夹着烟的手指微微颤抖了一下。他抬起头,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,又看向妈妈。
“晓晓,淑芬,”爸爸的声音低得像是在自言自语,“你们真以为,妈是在赶我们走吗?”
4.
我愣住了:“不然呢?那一巴掌还能是假的?”
爸爸深吸了一口烟,像是要把肺都呛穿,然后剧烈地咳嗽起来。
咳完后,他站起身,走到妈妈面前。
“媳妇,把大衣脱给我。”
妈妈虽然不解,但还是把那件深蓝色的工装外套脱了下来。
爸爸接过大衣,并没有穿上,而是把大衣反过来,伸手去摸衣领的内侧。
那里本来是有一层加厚绒布的,但此刻,我看到爸爸从衣领的夹层里——那个平时他用来藏私房钱的地方,费力地掏出了一个红布包。
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。
这件大衣自从出门后就一直穿在妈妈身上,爸爸是什么时候把东西放进去的?
不对,是奶奶。
只有出门前,奶奶最后一次经过衣架时,假装摔倒扶了一下这件大衣。当时我们都在气头上,谁也没在意。
爸爸的手颤抖得更厉害了。他一层层揭开红布,动作慢得像是在拆一颗炸弹。
随着红布落下,两样东西掉在了发黄的床单上。
一本皱皱巴巴的存折。
一张揉成一团的挂号信信纸。
5..
我凑过去看那张信纸。
纸上的字歪歪扭扭,一看就是奶奶那双颤抖的手写的,有些字甚至写到了格子外面。
纸条很短,只有几句话,却像一道惊雷,劈开了这个冬夜的迷雾。
“老二,老大在外面赌输了,欠了高利贷一百万。那帮人今天晚上要来收房子。他们那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黑心狼,说了要是拿不到房子就弄死全家。”
“带着淑芬和晓晓走,滚得越远越好,千万别回来!这存折里有八万块钱,是妈的棺材本,密码是晓晓生日。走!”
我感觉头皮一阵发麻,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倒流。
我抓起那本存折,打开一看,里面密密麻麻全是小额存取记录——卖废品的五块、十块,省下的买菜钱……
原来,她卖我的复习资料,是因为她在拼命凑钱;她嫌妈妈洗碗费水,是因为她想多攒一分是一分。
她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,甚至连那个暖水壶都想卖掉,就是为了给我们留这一条后路。
“爸……”我的声音开始发抖,“那刚才……刚才那一巴掌……”
爸爸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,大颗大颗地砸在床单上。
“那一巴掌,妈是在救你们的命啊!她怕你们不肯走,怕我也犯倔,她只能演这一出戏,逼着我们断绝关系!”
我突然回想起刚才的画面——
奶奶打完那一巴掌后,藏在身后的右手剧烈颤抖,那不是气的,那是疼,是心如刀绞的疼。
还有爸爸那沉默的3秒。
他在看什么?
他一直盯着奶奶的手,还有厨房门口那块没擦干净的地板——那里有一个陌生的、带着泥浆的大脚印。
那是讨债人来踩点的痕迹!
“不对!”爸爸猛地站起来,脸色惨白如纸,“妈既然把钱都给了我们,把我们赶走,那她一个人留在房子里干什么?”
妈妈也反应过来了,捂着嘴尖叫:“她是想拿这条老命去守那个房子!或者是想……想替老大扛这个雷!”
爸爸抓起那件深蓝色的大衣,像疯了一样冲向门口。
“快!回去!今晚就是那个期限!”
6.
我从来没见过爸爸跑得那么快。
冬夜的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,但我感觉不到疼,心里只有无尽的恐慌。
我们冲回筒子楼的时候,远远就看见家门口围着一群人,还有手电筒乱晃的光。
“老太婆,冤有头债有主,你那大儿子签了抵押合同,这房子今
发布于:湖北省鼎合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